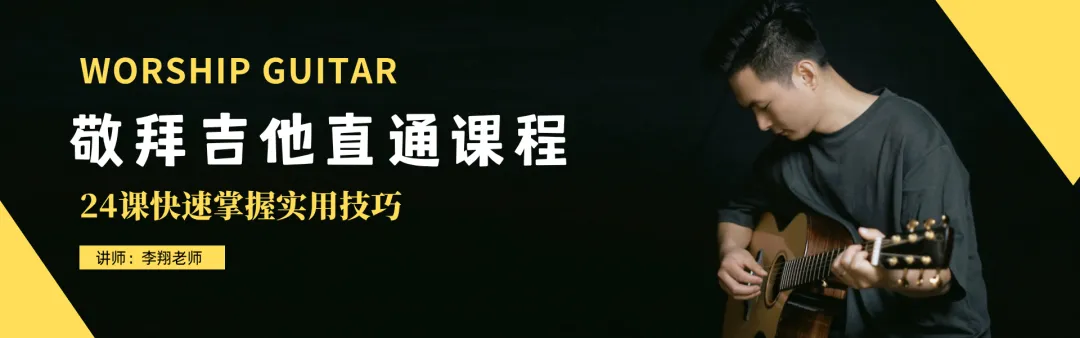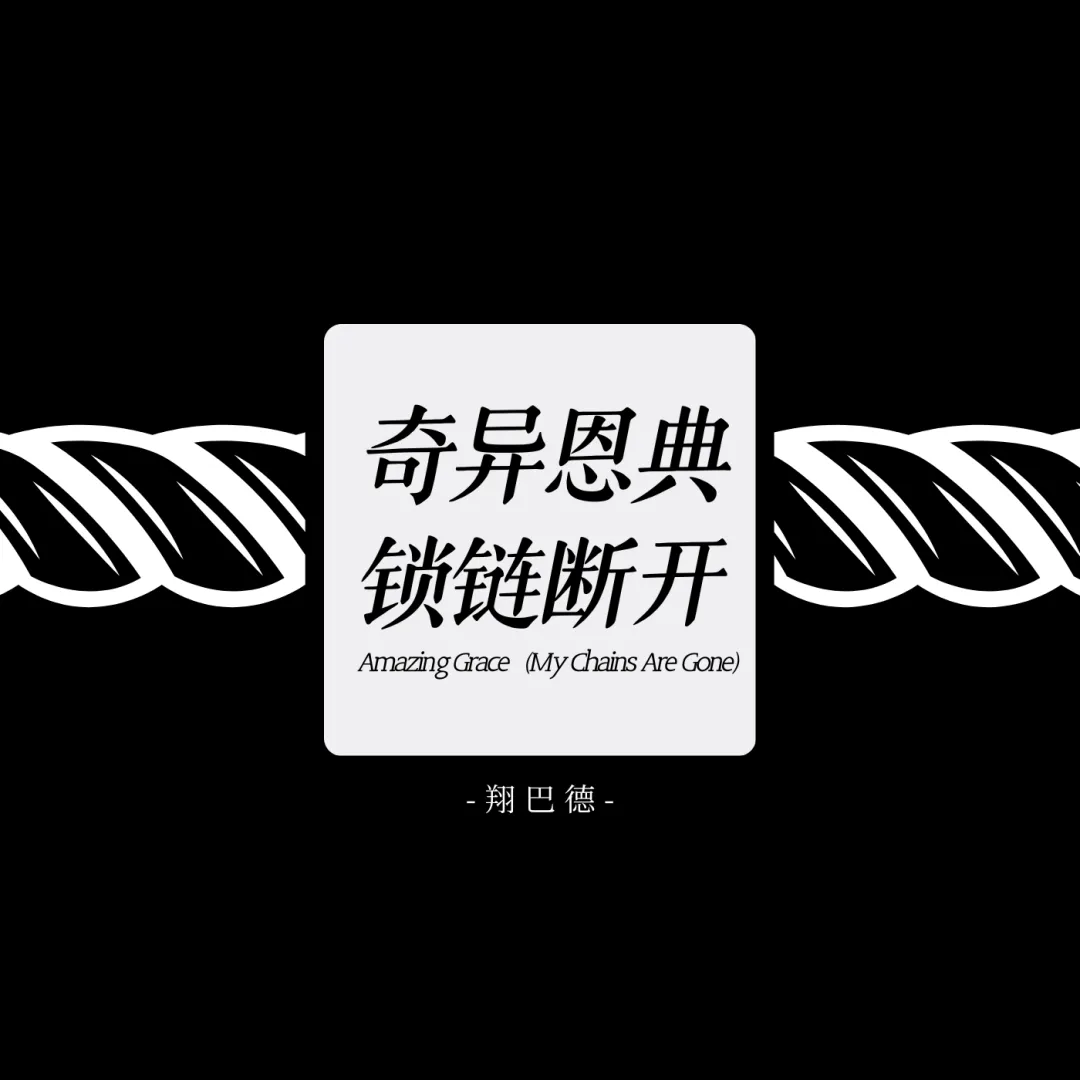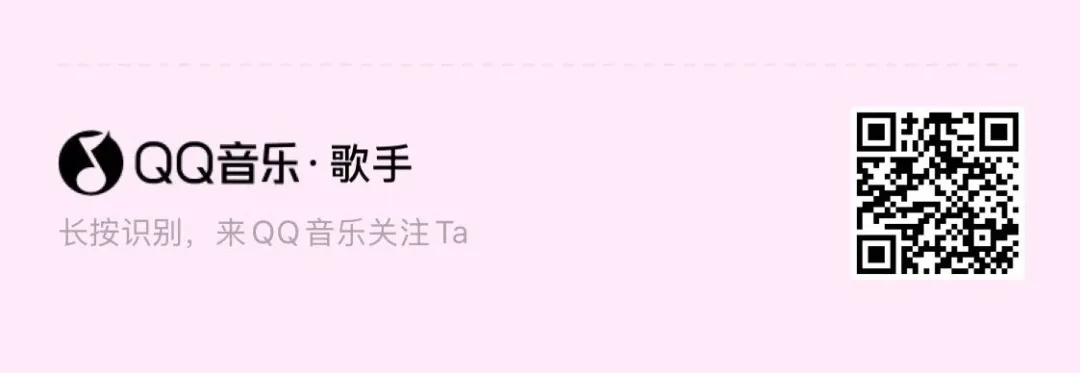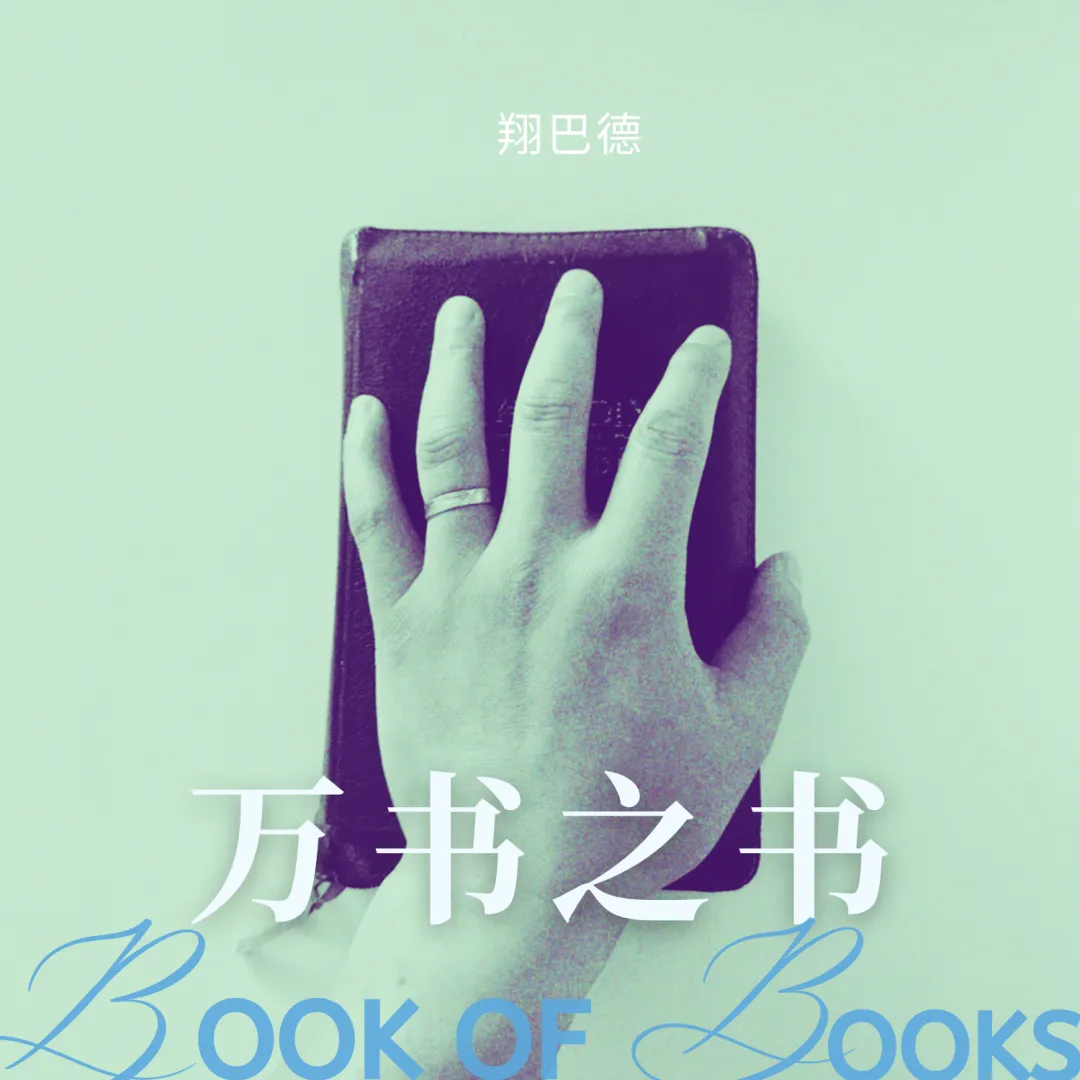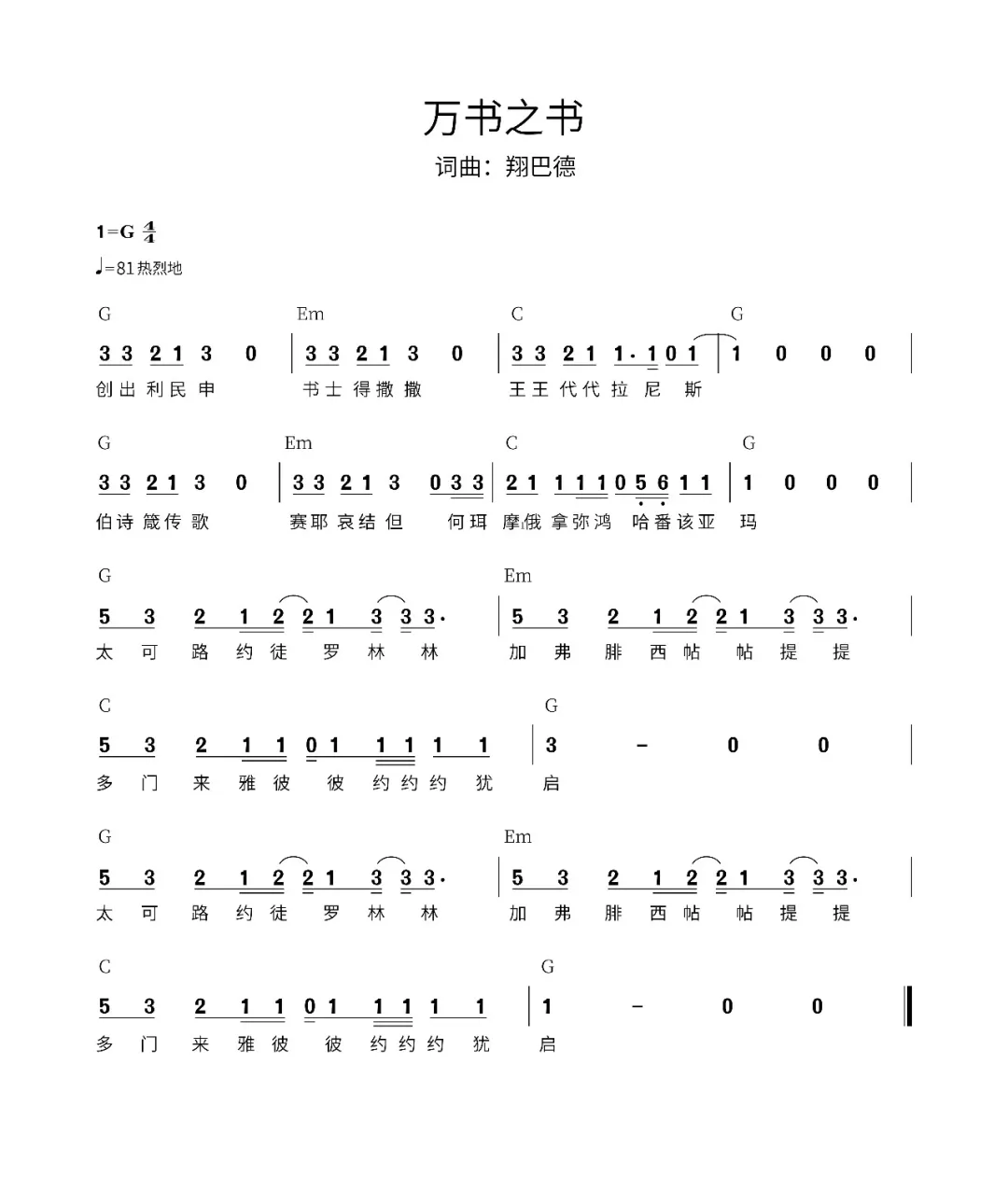上周六晚上,我发朋友圈说我的老战车开去正式报废了。
那是我的上一部车,买的时候已经是二手,后来它仍然还陪伴我们这个小小的利未团队走过了整整10年。
你在我的朋友圈留言说:也是挺耐造的了。
是的,你在上海的时候每周都会坐这部车,一转眼你回成都已经7年了。
第二天早上,我分享了《启10:6》:“不再有时日了”。
我说:“不要认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,那位掌管万有的随时都可能说没时间了,也许是我们的生命没时间了,也许是这世界没时间了。”
结果下午,我就收到了你车祸归天家的消息,你就这样不辞而别,在你给我留言的那个晚上。
我不敢相信,无法接受,这位比我还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弟兄就这么走了。
兄弟,多么希望你可以耐造一点!
虽然你的身体和我那辆车同一天报废,但车报废了就没了,你却还有永恒的生命,你如今到了永在的父那里。
想到这,我突然就没那么悲伤了。
/
2007年,同济毕业的你虽然在我们公司没有做多久,但是非常感恩,你在这里开始了你新生命的旅程。
还记得,我们几个搞音乐的新人弟兄,几乎要把台上的敬拜搞成了live house现场。
有一次聚会,是安排你弹电吉他,你一如既往的姗姗来迟,不仅没彩排,还迟到了5分钟。(数落数落你的囧事,在天上不要骂我啊)
我本来想过来跟你说:你这个态度,就不要弹了吧。
没想到你拿起吉他就开始接音箱,结果没经过变压器,把我那台从加拿大带过来的110V的Marshall音箱给烧了。
你没了声音,所以只能不弹了。
结束后我很严肃的和你说:是上帝不让你弹!
你开始学习了什么是敬畏之心吧?
/
但上海这个城市最终还是没能容下你这个充满艺术气质、不务正业(本行)的青年,在那个你皮鞋开了口的冬天,你回了成都。
我透过别人给你的钱你拿去买鞋了吗?
我感谢你,那次是你让我经历了一次信心的功课。
因为我看你的皮鞋开了口,前一周我通过奉献箱匿名奉献了800给你。
结果第二周我了解到你还没收到,但你马上就要走了,我摸摸口袋,发现自己只剩700,我纠结了一下,最终还是决定把700通过同工现场转交给了你。
但你知道吗?就在同一时间,我收到了一个装了1500的信封。而这件事情,我并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
我哭了,因为是TA知道我没有钱了,而这1500,其实是TA要给你的。
你现在终于在TA的怀里了吧,以后再也不用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了。
/
还记得那次你跟我说,你和一个姐妹谈恋爱了。我当时很为你高兴,我想不久我就可以参加你的婚礼了。
结果没过多久你电话跟我说,她和你分手了,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。
你和我说:我觉得上帝不够爱我,TA爱别人比爱我多。
我说:不可能,不信你现在就可以问TA。
我知道,你长期在保守的家庭里面成长,对于“聆听TA的声音”会有些陌生,但其实很简单,我想鼓励你试一试自己和TA建立关系。
我们挂了电话,我让你自己去问TA。
结果过一会你打了过来,我问你:TA怎么说?
你跟我说:TA说TA好爱我!
我听得出,你哭成了泪人。
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操心你的婚姻了,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最甜蜜、最伟大、最永久的爱。
虽然我没能等来你在地上的婚礼,但我相信将来我们会在羔羊的婚宴上相见,而且今天你也已经在羔羊的身边。
/
雅各说得对,明天如何,我们还不知道。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?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,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
你不是自己走的,是风把你带走了。
我们每个人都一样,风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也带走。
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再等,不要总说:等我有钱了,等我退休了,等我有空了…
一直在等的人,最终也许他们等来了他们想要的,但失去的往往是许多更宝贵的东西。
也许他们什么都没等来,而该失去的还是失去了。
盼望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被带走以后留下遗憾,而是要在没被带走的时候留下见证,成为云彩般的见证人。
/
所以,趁着白日,我们必须作那差我们来者的工;黑夜将到,就没有人能作工了。
白日就是那些能做工的时间,代表我们有机会,我们也有能力。
但黑夜来临的时候,机会就会被关闭了。
也许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,在我们迟延顺服的时候,在我们躺平摆烂的时候,黑夜就来了。
现在能做工,就赶紧做。
就如同我们这些利未人每周的工作,做一次就少一次,你不知道哪天机会的门就关了。
兄弟,你到天上的时候一定在拍大腿吧,肯定有很多工是你当做的时候没有做的。
我想我们每个人到那一天的时候都会一样,都会留下遗憾,但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做的事,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到那一天时遗憾可以少一点。
/
摩西曾说:“求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,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
有多少人懂得智慧是什么呢?
智慧不是知道很多,而是知道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重要的,所以懂了敬畏,就有了智慧。
而数算也不是计算自己日子还剩多少,因为没有人知道,数算是校准人生的焦点,排列人生的优先级,知道自己要把时间给谁。
我们年轻的时候,总会有很多事物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挥之不去,但我们可以更多追求TA,让TA更多充满我们更多占据我们,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为TA而活。
/
我们都是爱音乐的人,但是今天在天上的你,是否正在惊叹天上的音乐呢?
四活物的歌声,琴与炉的赞美令人赞叹吧!
原来我们弹的唱的那些东西若与我们的生命无关,根本达不到宝座前。
因为敬拜从来都不只是歌声。
保罗说,我们要将身体献上,也就是献上生命的全部,整个人生节奏与天上对齐,这才是好的敬拜。
今天,你在天上敬拜,我在地上敬拜,我们虽然离的有点远,但我相信,我们的声音一定会是合一的。
在地上,我们还有当跑的路,还有美好的仗,但总有那么一天,我们会在天上一起敬拜!
兄弟,我们天上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