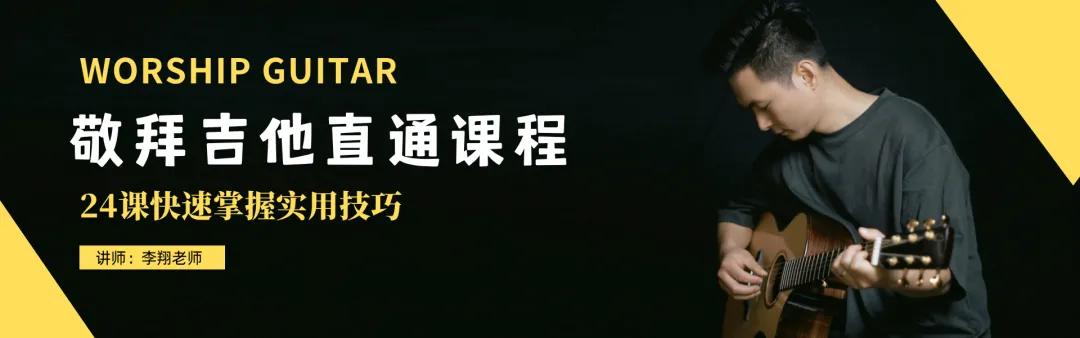那天我问一位当地弟兄:“你们每次都背这个包,里面装的是什么呢?”
他笑了一下,把包拉开给我看。
我看到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两本沉甸甸的书:一本是真理书,一本是诗歌本,都是傈僳文的。
当我捧着那两本神奇的书,就像是捧着一段沉重的历史。
那上面仿佛布满了这些人的指纹和汗滴——从富能仁、阿子打、约秀…还有无数不知名的人。
他们像接力一样,在这怒江大峡谷里,把这生命的火炬从一个时代传到了另一个时代。
这两本书为什么“神奇”?
因为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而是无数风雪、牺牲、坚持、眼泪、热血换来的,这是他们傈僳人的立命之本。
/
在怒江,这两本书就是傈僳族的精神源头。
在那个没有文字的年代,它给了傈僳族第一套系统文字,在动荡和压力下,它保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身份,在封闭贫困的大山里,它是傈僳人与全世界的文化交融。
长者说:“我们傈僳人,是被两本书改变的民族。”
当我翻开那本诗歌本时,我通过上面的乐谱辨认出了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诗歌,只是歌词部分被翻译成了傈僳文,例如那天听他们唱的就是那首《Bringing In The Sheaves/收成归天家歌》。
而那本真理书,对傈僳人来说更不只是一本书,它是生命的粮、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、永恒的盼望。
当年富能仁来到怒江时,这里没有文字,没有学校,也没有医院。山高、路远、贫穷、封闭,还有许多的黑暗和偶像势力,环境恶劣到超越想象。
但他带头做了一件伟大的事——给傈僳族创造文字。
没有文字,就没有教育;没有教育,就没有未来。
而阿子打更是把生命献在这里。她深入里吾底村,建医院、办学校、收孤儿,见一个救一个。
她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埋在了怒江,也把文字和音乐带进傈僳人的生活。
他们不只是“传入故事的人”,也是与傈僳人一同“写故事的人”。
后来,傈僳族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真理书和四声部诗歌集。
但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1949年后,这些外来的使者要不都埋在了这里,要不都离开了这里。但感恩的是,有本地工人约秀的一代兴起,他们传承了使命和圣工。
但1958 年起,礼拜堂被拆,聚会停止;后来再一次,所有书被没收、被焚毁。当时纯粹要靠着口传记忆,在夜里轻声颂唱、低声祈求,像是把火种藏在怀里。
他们没有书,但书刻在他们心里。
一直到1979年,终于可以开始恢复聚会了。
但傈僳人又面临新的问题:自由是有了,但没有书。
老仆人桑鲁斯和约秀,背着仅有的一本真理书和一本诗歌本,翻山越岭去到昆明,向相关部门申请印刷。
他们被拒绝、被反对、被质疑,但因着他们真沉质朴的坚持,最终,相关部门拨款四十万,用于出版傈僳文真理书和诗歌本。
第一批印了三万册,不够;于是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到今天不知道印了多少次,每次都供不应求。
如今怒江200多个村,就有600多个礼拜堂,而每个去礼拜堂的傈僳人,如今都能背着这彩色布包和里面这两神奇的书,去赞美崇拜。
对傈僳人来说,这彩色布包不是装普通东西的,它是肋下的盾牌、心上的信念、代代传下的火种。
每次背上它,就是把先人的故事和蒙福的记号背在身上,也成为了一个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见证。
那天,我寻思着我要去哪里买个这彩色布包带回去做个纪念,我问了几个弟兄,他们都说是自己家里姊妹做的。
后来在福贡县城逛了逛,也没见着哪个商店有卖。
第二天,神奇的事发生了,有位弟兄专程过来见我们,并送了我们一人一个彩色布包,还有一袋怒江咖啡。
我们的父真是太爱我们,傈僳家人们太爱我们,我们没开口,就知道我们心里的所想所求。
那天晚上,我们一群人都背上了这彩色布包,一起走在怒江边,边走边聊着这布包背后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