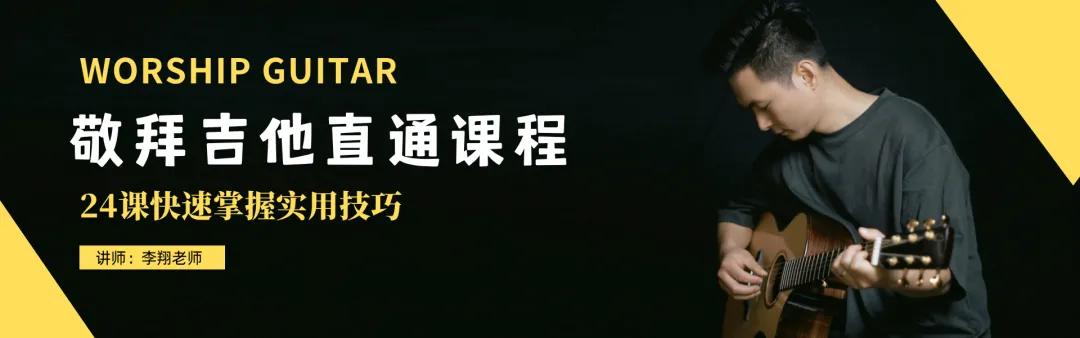富能仁的手提箱
文|翔巴德
这只手提箱是当年富能仁遗留下来的一件珍贵的遗物,1913年,富能仁就是提着它进入怒江大峡谷的。
第一次见到它时,仿佛见到了它的主人,我们都在想,它的主人当年都在箱子里装的什么,Bible、Hymnbook…
这只箱子在上海展出,感动了许多人。
这次,我们一群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要护送这只箱子回怒江福贡。
/
为了安全起见,给它提前打了木箱,因为箱子本身的重量就很重,即使是两个弟兄抬着它也走不了多远路。
我们定的是从上海飞往大理的航班,然后再乘提前包的车经过宝山去福贡。
这看似一段简单的行程,但从早上开始就变得“曲折”了起来。
开始飞机延误了1个半小时,然后因为大理机场大雾,所有飞机都迫降,我们的飞机被迫降至昆明机场。
到了昆明机场后,我们临时选乘高铁,而且还需要中途换乘。
因为箱子和我的吉他都是超大行李,等候行李花了很久时间,接着非常匆忙的坐包车赶往高铁站,中途只有很短时间换乘,几乎是分秒必争赶上了列车。
最后终于在晚上10点赶到了保山。
第二天一早,我们先去了富能仁墓地,然后中午紧接着一路开车赶往福贡,在盘旋的怒江大峡谷中又遇上了当天正在进行的马拉松赛事,一路堵车。
就这样,我们一路体验了各种交通工具后,各种折腾,终于在第二天晚上抵达了福贡,平安将这只手提箱物归原主。
/
我们一路都在感恩,因为同路人中没有一人有发怨言,后面想想,这点艰难与过去先人的旅程来比,又有什么资格发怨言呢?
当年富能仁要提着这只箱子,从伦敦出发,要漂洋过海翻山越岭。
那时的伦敦是世界的心脏,灯火通明。
他是帝国理工的高材生,生活优渥,按理说,他的人生该是一帆风顺。
但他却选择买了一张船票,向着当时地图上几乎空白的滇西进发。
他当时需要先从伦敦坐火车穿越法国或意大利,大约花费几天时间。那时来华的工人常选择马赛或热那亚港口,因为那里有前往亚洲的邮轮航线。
他登上邮轮,需要穿越地中海,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,再到印度洋,最后抵达缅甸仰光。
这段航程约需 3~4周,是极为漫长的海上旅程。途中常有酷热、颠簸、晕船等挑战。
抵达缅甸后,他需要再搭乘当地的铁路北上进入内陆。
铁路的终点通常是曼德勒或更北的景栋(Kengtung)方向。
而铁路无法继续深入中国边境,他得改乘马车或骡车穿越道路崎岖的山区。
这段路往往非常艰险,有丛林、泥泞、山谷、河流。路上可能需要几天到十几天。
在那时,进入中国西南的唯一方式几乎就是靠骡马驮队。他必须与当地商队同行,翻越高山、涉过河流,经野人山、盈江一带进入腾冲地区。
当骡马无法继续时,他只能徒步行走。
这一段是全程中最危险、最艰难的部分。富能仁曾多次提到在暴雨、蚂蟥、瘴气和饥饿中前行。
据记载,富能仁第一次抵达滇西的丽江—腾冲—保山区域时,是步行进入的。
他的鞋子常常破烂,夜里住在简陋客栈或山民家中。
进入滇西后,他还需多次步行、溯江、攀山,才能抵达主要服事地区。
比如我们从保山坐车到福贡都花费了6个多小时,可想而知当年没有马路,如果沿着怒江边走,那是多远多艰难的路程。
到底是什么,让他们这些先人愿意离开那样舒适的环境?让他们踏上如此艰难的旅程?
我想,一定是爱的回应,是崇高的呼召,是不得不“去”的感动。
/
在当年那片瘴气弥漫、山高路险、语言不通的土地上,富能仁发明了傈僳文字、翻译诗歌、教人识字。
他不是来被看见的,而是来让这里的傈僳族人,看见希望。
富能仁不是唯一一个走这条路的人,当年还有一批批的年轻人,从剑桥、牛津、芝加哥、悉尼、苏黎世出发,跋山涉水,穿越沙漠、丛林、山谷。
有人染病倒下,有人终身留在异地。
当我们的车行驶在怒江边狭窄的公路上,我透过车窗看到外面翻涌的江水,想到今天的我们,其实也是被邀请,要去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窄路,这过程中我们也会遭遇各样的艰难。
你有收到祂的邀请吗?你知道属于你的旅程在哪里吗?
或许不是跨越山河的旅程,也不是背着沉重木箱的跋涉, 而是在平凡的生活里,学会顺服、忍耐、相信与坚持。
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步,可能恰恰正是你的“窄路”。
我们今天回首百年前的脚印,不只是为了赞叹和感动而已,更是为了使命的延续。
从伦敦到怒江,从怒江到今天的我们。
每一代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窄路,我相信无论有多艰难,只要我们倚靠那位富能仁所倚靠的,我们就一定能走到目的地。
想起一首歌:明知这路,是***的路,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,祢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,没有任何理由,不去走脚下的路。
祝福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