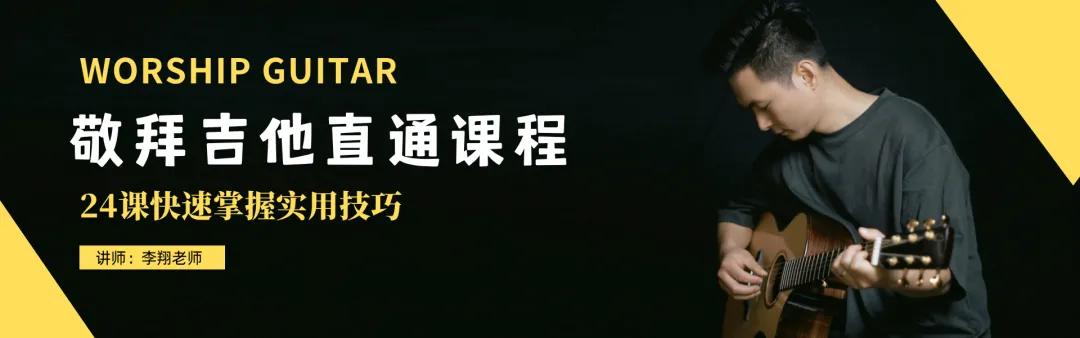有一种人,他们离开故乡的舒适圈,不为名,不为利,只是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度。
他们本是富足,却甘愿成了贫穷。
富能仁,James O. Fraser,他出生在英国伦敦,一个温暖又富足的家庭。
学业优异,音乐天赋惊人,若留在英国,他的人生注定光鲜。但他却背起行囊,来到中国云南怒江峡谷间,与傈僳族人同住、同吃、同唱。
没有电、没有路、没有语言,只有山雨、瘴气,还有那份从不动摇的呼召。
他曾写信说:“我不想只做一个送外人恩惠的施主,我要与他们一起得着那份生命的喜乐。”
他所“失去”的一切,成了另一个民族重生的希望。
英国医生之子戴德生,放下伦敦的舒适的环境,穿上中国长袍马褂,吃中国的粗茶淡饭,为的是让中国人明白:那份永恒的爱不是西方的,而是为所有人预备的。
剑桥七杰的施达德C. T. Studd,英国板球冠军,本可一生富贵,却把百万遗产全数捐出。
他说:“若祂为我而死,那我为祂而活,还有什么是可夸的呢?”
伯格理,走进贵州山中,发明了苗文文字系统,让一个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与书本。
他没留下财富,却留下了文化的觉醒。
他们的脚印穿过山川,也穿透历史的尘烟,从富足迈向了贫穷。这与许许多多为了追求富足生活而离开故土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这提醒着我们:真正的富足,不在拥有,而在给予。
/
有时我在想,“贫穷”这个词,是否被误解得太深。
他们的贫穷,不是匮乏,而是一种自愿的倒空。
他们不是被迫失去,而是主动舍弃——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。
富能仁的日记里写过:
“当我弹起破旧的小提琴,看见山谷里的人跟着唱时,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美。”
这种“贫穷”,比任何财富都更丰盛。
因为他们富有音乐,却不为舞台;富有知识,却不为名誉;富有爱,却不为自己。
他们的生命,就像一粒种子,落在泥土里,表面消失,却在地底死了,发芽,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
一代又一代人,在他们倒下的地方,仍旧长着希望。
/
一个世纪过去,他们的故事听来几乎像传说。
但我常想,今天的我们是否还存在这种一粒麦子“倒空的勇气”?
也许我们不必远赴高山、跨越海洋,但那份“为人成为贫穷”的精神,仍然在今天呼唤着我们。
这世代太习惯追求“拥有”,但这些先人的故事提醒着我们,拥有的终将失去,唯有“给予”,才会留下。
他们并非不爱生命,他们是太爱了——爱到愿意让生命成为更大的出口。
正如有人说:“世界被少数倒空自己的人改变,而不是被那些努力充实自己的人改变。”
如今,怒江的山谷早已有了电灯,苗乡的孩子也能读写自己的语言,中国的城市也早已与世界相连。
那些名字或许被遗忘,但他们燃起的光,仍在延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