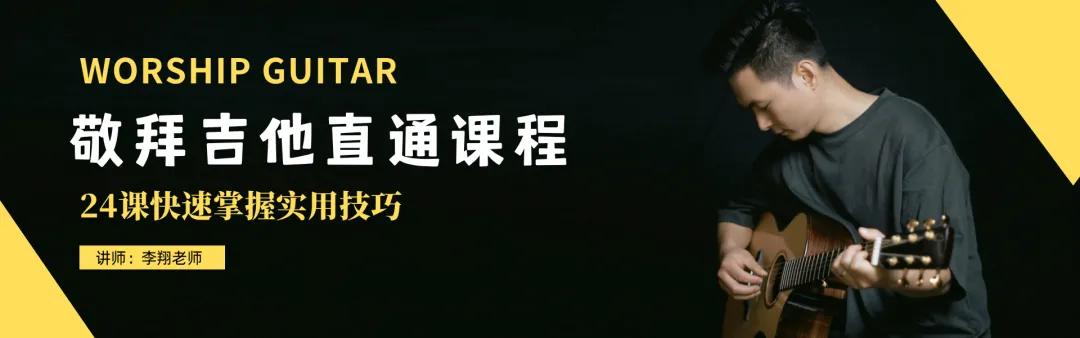南接子里甲乡俄科罗村,东邻腊母甲村,西边连着缅甸,北面是架科村。全村 7 个村民小组,744名村民,全是傈僳族。
“里”是傈僳语的竹排,“吾”是最先,“底”是“顶”的变音,意思是停放的地方——整个村名,就是“最先停放竹排的地方”。
因为靠着怒江,这里曾经是渡口,常年停着渡江竹排,便有了这个名字。
那天,我们来到这里。
如今的里吾底,安静、温柔,且深藏着许多美好的故事。
这里埋着三位外国人,这些故事都和他们有关。其中一位,就是被傈僳人称作“阿子打”的伊丽沙伯。
/
去往里吾底的路就像一首难唱的傈僳诗歌,对我们这些城市乡巴佬而言,用“连滚带爬”来形容一点不为过。
那天,我们驾车到半路,然后跨过石堆,翻过山路,最后坐上三蹦子, 开了不知道多少个坡,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,最后终于抵达村里。
当我们进村时,虽然也能看到一些现代化的建设,例如现代的房屋和篮球场,但仍然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,仿佛是一百年前就停在这里、从来没被时代打扰过的宁静。
这条路,在百年前,阿子打与阿益打夫妻,也曾日复一日地走过。
但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,要到一个村寨,需要走山、走林、翻坡,一座山头过去才发现,还有一座,全部只能步行。
我们来了,当天就走了,而他们,选择住在了这里。
“没有一个外面的人能在里吾底住几十年,”阿子打的学生阿普加曾说,“他们来的时候,就已准备老死在里吾底。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。”
不是因为这里很舒适,而是因为:这里有一群傈僳人,他们需要生命。
/
来自美国的阿子打,是里吾底人给她的尊称——“尊敬的大姐”。
她几乎是村里的全能手:护士、老师、园丁、音乐家。
她家是小小的医疗站,村民生病了来找她,妇女怀孕了,她主动去关心;生产时,她亲自接生。
有人记得她当年提着简单药箱、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背影。
她不仅给人治病,也教导真理,让许多傈僳人从害怕鬼怪的恐惧中进到光明的国度。
晚上,她会教孩子傈僳文、算术。据说,孩子们背下课文,就给糖果或铅笔。白天,她种菜,也教村民种菜,村子里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菠菜,就是她带来的。
傈僳人天生会唱,山谷里本来就回荡着歌声,但因着阿子打的到来,这里的歌声从山歌变成了赞美的诗歌。
她与丈夫阿益打翻译完福音书,就翻译赞美诗,一笔一画地写谱,教村民唱。
如今傈僳人的歌声能在怒江峡谷的每一个山头回荡,都是从阿子打和里吾底村这里传开的。
/
1944 年,阿子打在去南安甲服侍的途中,因为过度疲累,旧伤发作,感染发炎,被搀着回家。
那时里吾底没有足够的护理,最终她在那年4月安静地离开。
在墓室的墙壁上,刻着她丈夫阿益打的回忆:
“这些僳僳人在安葬我的妻子时,流着眼泪为她唱《复活歌》,每天有好多人来安慰我,回忆阿子打生前的各种往事,好多人都哭了。傈僳族真是世界上最善良、最有同情心的民族。”
/
那天,我们站在阿子打墓前,唱起了《一粒麦子》:
这不只是一段旋律,而是在这里真实发生的故事。
我在想:一个人选择把生命摆上,会发生什么?
答案就在眼前:一整个怒江峡谷被唤醒,一整个傈僳民族被拯救,以及成千上万的生命故事。
/
今天的我们,所拥有的恩赐、才干、金钱、能力或许都比阿子打要多得多,医术比她更高超,音乐比她更擅长,经济比她更富裕,但我们缺少是成为一粒麦子的勇气和决心。
麦子并不需要有多伟大,它只需要愿意:
愿意落在一个不舒适的地方,愿意被埋在别人看不见的土里,愿意在黑暗中忍耐,愿意在风雨中等待——直到发芽。
阿子打只是一位愿意的人,她的能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,但我想她从未想过,她的生命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,它的死会结出如此多的子粒来。
因为这一粒麦子的愿意,改写了怒江和傈僳人的历史。
/
下山的时候,我们去探访服事了一位生病的家人,临走时我们和这家人说“再见”,家人笑著说:不会再见了的,你们肯定不会再来这里的。
我的鼻子突然一阵酸楚,我知道此刻的我就是一个观光客,服事也只是顺道而已,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舒适的大城市,我们除了在DG中纪念,还能为他们做什们呢?
坐上三蹦子,吹着下山的风,看着两边摇动的竹林,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我想:
也许再也不会有如此深爱傈僳人的阿子打和阿益打了,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“里吾底”,和属于我们的“傈僳人”。
我们要在那里生活、服事、燃烧自己,像一粒麦子一样也在那里埋葬自己。
你的里吾底在哪里?你的“傈僳人”又在哪里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