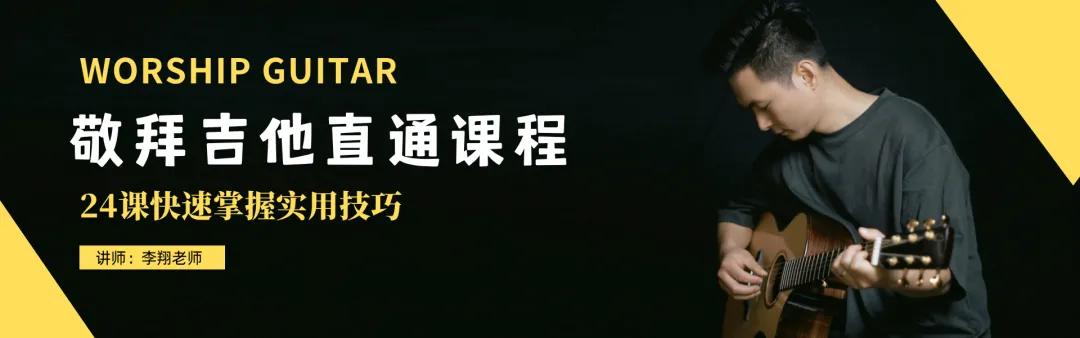雨后的怒江峡谷被薄雾笼罩,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泥土气息。
我走在这座吊索桥上,脚下铁板上的水迹里隐约有着山的倒影,桥索在风里微微的晃动,能听到鸟儿在上面歌唱的声音,还有桥下传来的江水声。
前方,一个穿着傈僳族服饰的老人正缓缓的向对岸走去,身上背上一个他们傈僳族的彩色刺绣手工斜挎包。
他的脚步不急不慢,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岁月的节拍上。
桥的另一端,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。他穿着套头卫衣和工装裤,戴着耳机,脚步轻快,脸上带着都市人的神情。
当他们两人在桥的中央擦身而过时,我心头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/
从远方走进山谷的一代
一个多世纪前,一个年轻的英国人,提着那只手提箱,第一次踏入这片峡谷,那是1913年的夏天。
他名叫富能仁。
那一年,他才二十七岁,刚从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毕业。原本他可以留在欧洲,成为一名工程师,拥有体面的职业与安稳的生活。
但他的心却被远方吸引——那个地图上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方:中国滇西。
他一路跋涉,翻越高山,穿过激流,带着书、琴,还有那只沉重的提箱。
富能仁深知自己只是暂时的过客,他更盼望本地人能自己兴起,让信仰在这片土地上落地、生根、结果。
于是他发明文字、翻译歌本和真理书、办学堂、教文化,更重要的是——培养了一批一批的本地工人。
他曾写信回家说:“外来的工人总有一天会离开,唯有本地人自己兴起,才能薪火相传。”
富能仁的眼光,远比他当时的时代更深远。他没有急着盖宏伟的教堂、也没有留下雕像,他留下的,是“人”。
那些被他教导、训练、陪伴的傈僳青年,成了后来怒江史上的第一批本地工人。
/
约秀的一代
与富能仁一同做工的杨思慧夫妇领养了一个傈僳族孤儿,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得力助手,他的名字也常被人提起——约秀。
他是怒江第一个被按立的傈僳牧者。
约秀那一代人,走的路更艰难,他们要翻山越岭,跨过江河,带着好信息进到每个村落。
他们没有乐器,也没有音响,但他们却让最真挚的赞美在山谷回荡,从里吾底,到各个村落。
那是他们最初的声音,没有修辞,只有生命。
他们在竹屋里聚会,雨天的地上全是泥,但他们的歌声却没有止息。
他们继续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歌唱,继续培养和训练工人,直到今天几乎大部分的族人都相信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位。
/
今天的一代
“一代过去,一代又来,地却永远长存。”—《传》1:4
时间流转,一个世纪过去了。
如今,怒江的峡谷里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寂静。
一座座吊桥成了连接各村的要道,汽车、摩托车、三墩子在峡谷间穿梭。
许多年轻人走出了山谷,也有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了这里。
我站在这桥上,望着那位老人远去的背影,他的步伐有些蹒跚,但目光坚定;而再看那个年轻人,步伐轻盈、神情自信。
两个人,一个即将成为过去,一个正在走向未来。
他们在桥上相遇、擦肩,却都继续前行。
旧的信心与新的能力,在同一条路上同行。他们不需要完全相同,但他们都在走向属于他们的彼岸。
上一代的终点成为了新一代的起点。
/
传承不是替代,而是延续
富能仁的一代,是“开路”的一代。他们从远方来,为滇西点亮了第一盏灯。
约秀的一代,是“扎根”的一代。他们让信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长出枝叶。
而今天的这一代,是“继续走”的一代。
他们不需要一直重复讲述旧的故事,因为他们会有属于他们的故事。
无论是上一代,还是下一代,他们都是在延续着祂的故事。
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使命,就像这座桥——每一根铁索,都是一条献上的生命,都是在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。
结语
当那位老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处,那个年轻人也与我擦身而过。
我在想,我们这一代也终将走到桥的尽头,但那绝对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代的起点。
这时,约秀的孙辈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到了,我们开着车在峡谷间穿梭,一路上聊着他们青年人的赞美敬拜和傈僳文歌曲的创作发行。
江水依旧在脚下奔流,仿佛在告诉我:一代过去一代又来,但祂的爱如江河永不止息,我们的赞美也要永不止息。